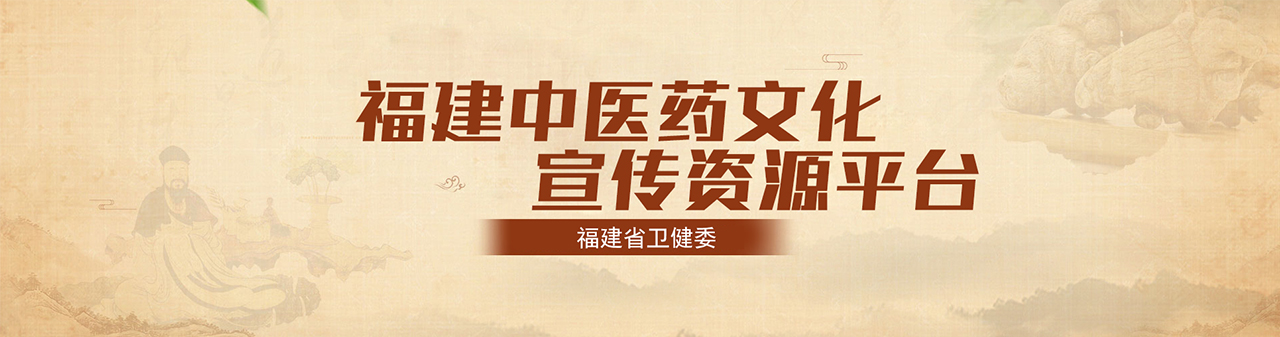青年中医师的成长之路正面临着双重挑战。诊室里亟待突破的临床能力提升瓶颈,人才评价体系中无法回避的科研指标,成为笼罩在青年中医心头的迷思。他们试图用每一次把脉开方,寻找到属于自己的临床坐标。
近日,中华中医药学会青年委员会搭建对话平台,邀请多位青年中医师直面这些“成长的烦恼”。在他们身上,我们既看到岐黄之术薪火相传的希望,也窥见中医现代化转型之变。
真金不怕火炼 临床经验是熬出来的
“当我发现一些因疗效不好,患者不来复诊以后,我的内心总是充满不甘与困惑。”北京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青委会副秘书长万宇翔坦言,他在跟随中医肿瘤名家黄金昶教授学习的过程中逐渐领悟,“厚着脸皮”追问到底的执着精神,或许比天赋更重要。
“患者是医生最好的老师。年轻医师最怕的不是犯错,而是错过成长的机会。”万宇翔说,这种反思精神,是一位中医人从青涩走向成熟的必经之路。
“从硕士阶段,我就意识到中医临床是不断学习的过程。”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儿科主治医师陈海鹏回忆,遇到疗效不佳的病例时,挫败感促使他持续学习。一个顽固性咳嗽患儿让陈海鹏对中医辨证有了更深的体悟。患儿初诊呈热象,辨证为湿热咳嗽夹外风,用麻杏石甘汤、三仁汤合祛风药后好转六成;复诊转为痰湿咳嗽夹外风,改用二陈汤合祛风药却收效甚微。“追问病史,患儿加重的诱因是喝冷饮,这时我才意识到证候已转为寒象。我在原方基础上加干姜、细辛,最终患儿治愈。临床实践教会我,必须回归中医本源,明辨寒热阴阳。”陈海鹏说。
陈海鹏特别强调青年中医要培养两种重要心态:“一是要有‘坐冷板凳’的定力。必须保持钻研的韧性。二是要建立坚定的专业自信。要相信终会找到正确的治法,这种对中医的信念感尤为重要。”
“熬”,是许多青年中医在成长之路上的共识,正如熬煮中药需要文火慢炖、耐心守候,中医临床经验的积累也需经历岁月的沉淀与磨砺。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主治医师张凯歌坦言,临床之道,从无捷径。唯有如同炮制良药般,将身心倾注于临床这方“药罐”之中,历经“文武火”的反复煅烧与淬炼,方能凝萃出治病救人的真功夫。此般“熬”炼,不是消磨以待,实乃沉潜涵泳;不仅是循环往复,更是厚积薄发。
“我们都是从年轻中医一步步成长起来的。”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张冰回忆当年跟师经历,对当下青年中医的焦虑格外理解,“那时候老师让我们读梁启超的书,啃张元素、朱丹溪的典籍,我们心里也憋着一股气,觉得这些老古董有什么用?可如今回望,正是这些看似‘无用’的积累,才在关键时刻救了我们。”
无须谈“卷”色变 中医思维是练出来的
当前,科研压力与临床成长的双重夹击让不少青年中医师谈“卷”色变。
陈海鹏表示,在当下医疗环境中,青年中医师无须对“内卷”过度焦虑。“当我们将目光重新聚焦于中医本源,也即阴阳平衡、寒热虚实时,中医的独特价值才能真正彰显。”陈海鹏说。
重庆市中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肖月园认为,中医临床的精髓不在于掌握多少“验方绝招”,而在于培养辨证思维的逻辑体系。
“我们容易陷入一个误区,”万宇翔认为,“遇到疑难病例时,第一反应是回忆老师用过的某个方子,而不是分析当下的证候机理。”这种“方证对应”的碎片化学习,虽然能快速解决个别问题,却难以形成可持续的临床思维能力。
“在临床实践中,如何实现对中医经典和古今中医理论与临床的观照思考,是我们青年医师需要注意的问题。”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内科主治医师任北大表示,当思考足够细微,对实践是非常大的促进。这种和古人跨越千年的对话、思考和交流,为把握临床实践方向规律、做好经典和临床的结合文章提供指引。青年中医的立身之本,就在于持续回归中医本源,在每一次辨证中打磨自己的中医思维。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重症医学科副主任医师陈腾飞刚过而立之年,却已在带教“00后”学生。在重症医学科躬耕,他深知中医思维对青年中医人成长的重要意义。“我们的ICU现在就非常注重中医思维主导下的危重症救治理念,中医思维会贯穿每一位青年中医人的学习生涯。比如严重感染会导致多脏器的衰竭,但各个脏器之间并不是孤立的,而是有相互作用。中医整体观有先天思维优势。”
肖月园认为,深入研读并背诵中医经典是培养思维的基石,不仅要理解其理论精髓,更要将其内化于心;跟随名师学习则是传承中医智慧的桥梁,要珍惜学习机会,以谦逊的态度求教;临床实践是检验理论的试金石,要将所学知识应用于实践,实现知行合一;勤于思考是提升临床思维能力的必要方法,要不断反思与总结经验。